圣誕檔期內(nèi)地電影市場創(chuàng)15年新低,票房僅8026萬元,原因何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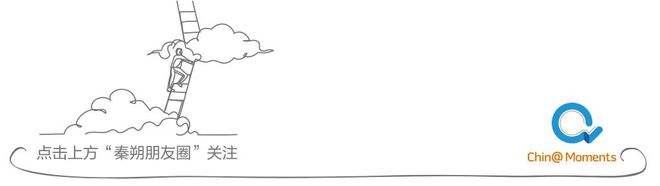

頭圖由豆包生成,提示詞:圣誕電影
剛剛過去的圣誕檔期,內(nèi)地電影市場創(chuàng)下了近十五年以來的最低紀(jì)錄,票房總額為8026萬元人民幣(即平安夜與圣誕節(jié)兩日,含服務(wù)費)。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國內(nèi)銀幕數(shù)只有六千塊,而現(xiàn)階段這一數(shù)字則在八萬塊左右。
電影數(shù)據(jù)的大幅下跌,引發(fā)了廣泛的關(guān)注,畢竟這是一個理論上最受益于口紅效應(yīng)的行業(yè)。
可在針對影市遇冷的分析中,放眼望去盡是荒腔走板的外行論調(diào):有的倒果為因——如沒有新片上映;有的不懂裝懂——如電影質(zhì)量不行;還有的盡顯幸災(zāi)樂禍之能事——如電影干不過短劇。
以上說辭以其不專業(yè)的程度來看,原本不值得一辯,無非是本就不看電影的人在相互印證自己的偏見。但由于它確實能在“小圈子”里“蠱惑人心”,造就一批自以為是的“懂王”,又還是存在略作澄清的必要。
我記得王小波說過一番話,大致意思是,每當(dāng)碰到有人裝蒜,就一定得有人出來說一些令他不舒服的話,不是為了改變他,而是要讓這種人知道,大放厥詞是有代價的。
影評人波米對2024年圣誕檔數(shù)據(jù)滑坡的分析極具建設(shè)性。
首先,他認(rèn)為“大盤缺新片”的說法是因果倒置。
真相不是沒有新片上映,所以檔期拉垮,而是檔期先垮了,所以沒有新片涌入。
其次,他認(rèn)為國內(nèi)的圣誕檔在2021年就已經(jīng)名存實亡。
之所以今年才被大家意識到,是因為前兩年的平安夜恰逢周末,尚有“非工作日”這個遮羞布。而一個成立的檔期,完全可以排除工作日與非工作日的影響,顯而易見的是,如今的圣誕檔已經(jīng)不能做到這一點。
那么,2021年的圣誕檔到底發(fā)生了什么呢?
頭一件事,是電影《長津湖》超越《戰(zhàn)狼2》成為中國影史票房冠軍,并造就了一句影響至今的網(wǎng)絡(luò)流行語——“看完《長津湖》,再無圣誕夜!”

說到這一點,我可以提供一樁近日經(jīng)歷作為參考。
平安夜當(dāng)天打車,剛一上來,司機非常健談地聊起了圣誕,說上海今年的節(jié)日氣氛很淡,幾個熱鬧的商區(qū)幾乎沒客人。
我問:“你覺得是什么原因?qū)е碌摹!彼緳C講:“你沒刷到《長津湖》和平安夜的短視頻嗎,我一打開手機都是這些。”我告訴他:“那是因為你看完了這個視頻,算法就會一直給你推同樣的內(nèi)容。”
在我看來,這場意外的對話其實是一個驗證電影媒介屬性的鮮活案例。都說沒人看電影,但一部電影在社交媒體的持續(xù)發(fā)酵,甚至?xí)钜粋€重要節(jié)日的商業(yè)活動降格。
這一點,游戲做不到,短劇做不到,短視頻僅靠自己的站內(nèi)內(nèi)容也做不到。
2021年圣誕檔的第二件事,則是電影《平原上的摩西》在預(yù)售票房大好的情況下宣布撤檔。
雖然出品方已將片名里的“摩西”改成“火焰”,但仍未避開好事者的口誅筆伐。《平原上的火焰》的臨時撤檔,在業(yè)界引發(fā)了一輪寒蟬效應(yīng),令后續(xù)的重磅新片不再選擇圣誕檔發(fā)行,這宣告了這一傳統(tǒng)賀歲檔的事實性消亡。

在這兩部電影一揚一抑的際遇之間,也正貫穿了近年影市起伏的隱秘線索。
在我看來,當(dāng)前導(dǎo)致中國電影市場票房不佳的矛盾主要有三點。
其一,是持續(xù)數(shù)年的疫情,令電影行業(yè)沒有生產(chǎn)“重工業(yè)大片”的條件,客觀上導(dǎo)致了賣座電影的供不應(yīng)求。
這一周期性的困難,會隨著時間自然緩解。在馬上到來的2025年春節(jié)檔,就已經(jīng)定檔了《封神第二部:戰(zhàn)火西岐》《哪吒之魔童鬧海》《唐探1900》等多部足以拉動觀影人次的A級商業(yè)片。
其二,是產(chǎn)業(yè)下游的不確定性增加,法定流程受輿論干擾嚴(yán)重,表現(xiàn)為取得公映許可且進(jìn)入院線發(fā)行的電影,常于公映前撤檔。
當(dāng)然,一些片方基于錯綜復(fù)雜的商業(yè)考量,也會選擇主動撤檔。但越是那類制作與宣發(fā)費用都很高的項目,越不可能借由更換檔期炒作。原因很簡單,選定的檔期往往都是有講究的,宣發(fā)上投出去的成本也會被白白浪費。
大片的操盤手,最看重的東西就是確定性。而電影市場所能創(chuàng)造的價值多寡,也依賴于規(guī)則機制是否穩(wěn)固。如果市場遍布不可知的意外風(fēng)險,那就相當(dāng)于變相驅(qū)趕長期參與者。
簡單說就是,越是大片,越折騰不起。小片還有概率投機取巧;可幾個億投資的大片,一旦灰飛煙滅,對產(chǎn)業(yè)的負(fù)面影響便難以估量。
所謂“尊重創(chuàng)作者個性,尊重電影產(chǎn)業(yè)規(guī)律,營造開放、公平、法治化的投資環(huán)境”,能否真正貫徹落實,決定了第二個矛盾到底是一輪周期還是一股趨勢。
其三,則是充滿戾氣的輿論生態(tài),這一來自網(wǎng)友的阻力,同樣會反向作用于上游生產(chǎn)者與相關(guān)管理部門,而它亦是在增加市場的不確定性。
越來越多的吃瓜群眾,希望在一部電影上映前就掌握評判權(quán)。
一個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是《封神第二部》推出第一款預(yù)告片后,便有人拿著預(yù)告片里的截圖在網(wǎng)絡(luò)開黑,主題直指特效廉價,稱魔家四將的效果看上去不如《黑神話:悟空》的相關(guān)造型。

為什么說這種指摘非常輕浮呢?
要知道一個魔幻、史詩性質(zhì)的視效大片,預(yù)告片和正片的效果相差甚遠(yuǎn),說是兩種東西也不為過。
精良的特效需要大銀幕去呈現(xiàn),且不說IMAX銀幕或其他規(guī)格的巨幕,至少得是一塊正經(jīng)的電影銀幕,這不是電視屏幕或手機豎屏可以比擬的。一張截圖看著不好,那是手機只能呈現(xiàn)出那種效果。就好比拿著望遠(yuǎn)鏡去看巨人,四大天王在鏡頭中也不過是土行孫。
所以,這不是一個審美問題,而是一個智識問題。
另外,游戲和電影對特效的要求不一樣,對人物造型的要求也不一樣,拿游戲類比電影本身就驢唇不對馬嘴。試想《黑神話:悟空》問世的時候,如果86版《西游記》的原著粉以劇集里的設(shè)定去抬杠,給它各種扣帽子,這款游戲還能收獲那么多好評嗎?
何況對于電影來說,特效只是內(nèi)容完成度的其中一個方面,因為特效而提前批評一部沒有上映的電影,實在是膚淺而草率的行為。
類似輿論干擾風(fēng)評的現(xiàn)象,還存在另一個趨勢:即在商業(yè)片和文藝片中批商業(yè)片,在大成本與小成本中批大成本。
比如同樣是講國內(nèi)的外賣行業(yè),徐崢導(dǎo)演的《逆行人生》上映后就惡評如潮,而新導(dǎo)演劉泰風(fēng)的《又是充滿希望的一天》就收獲了整齊劃一的好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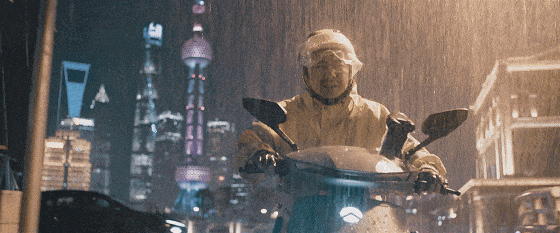
這兩部電影我都看過,應(yīng)該說角度不同,各有表意——前者著重于表現(xiàn)人的困境,是心理派的典型拍法;而后者則深入困境背后的運行機制,有著鮮明的社會派屬性。
實事求是地講,從類型的完成度與主題的豐富度來看,顯然是《逆行人生》做得更好,這不是兩部電影拍法的優(yōu)劣,只是創(chuàng)作者具體經(jīng)驗的厚薄。
然而,我的這一觀察,并不契合兩部電影同期上映時的口碑。造成這樣的結(jié)果,固然有評價人數(shù)所起的作用,但也存在一個簡單粗暴的打分邏輯:《又是充滿希望的一天》是文藝片,而《逆行人生》則是商業(yè)片。

這一代網(wǎng)友身處被污染的信息環(huán)境,普遍具有一種預(yù)設(shè)的立場,即對資本、商業(yè)、公司、市場等概念不以為意,一部電影只要被扣上了這些元素,仿佛就是不懷好意來圈錢的垃圾。與之相對,只有那種幾乎無人問津的賠錢之作,才值得他們?nèi)ズ煤谜湟暋?/p>
但真正會去電影院的觀眾都明白一個道理:電影的質(zhì)量和規(guī)模、類型、屬性沒有必然聯(lián)系,一個大投資的電影也可能極具藝術(shù)價值,一部小成本的電影也有概率是徹頭徹尾的垃圾。
正是由于以上幾點矛盾的存在,使得當(dāng)前的中國電影無法充分發(fā)揮競爭優(yōu)勢,其票房潛力被大大抑制了。
其實以中國電影2024年的概況來看,幾乎每個月份都有好電影,類型之豐富、品類之多樣、風(fēng)格之多元,甚至超過往年。不僅如此,在進(jìn)口片的審批方面,過去的一年也大開綠燈,為中國觀眾引進(jìn)了不少海外佳作。
有些人對這一現(xiàn)狀感受不到,那是因為他們壓根就不關(guān)心電影,只會裝模作樣地點評“沒有好電影”,可你問他什么是好電影,他八成只會啞口無言。
但問題又來了,為什么今年上映了這么多電影,卻無法有效提振票房呢?答案就是前面說過的:因為它們大多是豐富市場的輔助元素,卻不是振興市場的生力軍。就像一個人只吃配菜不吃主食,過后很快就會餓。
我們并不是缺好電影,只是缺能夠吸引大眾入場的主流商業(yè)大片。如何把中國電影的主食重新端上桌,造就一席饗宴,則需要全社會往正確的方向加把力、不回頭。
No.6146 原創(chuàng)首發(fā)文章|作者 臧否
開白名單 duanyu_H|投稿 tougao99999|圖片視覺中國/豆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