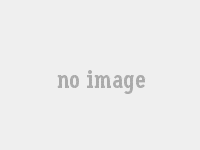馮志陽︱傳統(tǒng)社會(huì)日常生活中的生與死
晚清著名商人徐潤在自敘年譜中有這樣一段文字:
先叔好談風(fēng)水,闔邑?zé)o不知之。二三年內(nèi)用洋十余萬,每日堪輿家茶點(diǎn)、轎金二三十元,查置山地費(fèi)總需萬金,計(jì)山地一百余處。如葬高祖東星公于沾涌,計(jì)費(fèi)三千元,曾伯祖卿佳公葬于前山后龍,伯祖云忠公、圣忠公、玉書公葬在倒地木,每山約費(fèi)五六百元。曾祖卿禮公葬于麻灣村后山,計(jì)費(fèi)二萬元,先祖誠齋公葬澳門石角嘴,計(jì)費(fèi)二萬元,此二山為全邑之冠,故費(fèi)用亦獨(dú)大。先祖母容太夫人壽基在造貝嶺,庶祖母李宜人葬三臺(tái)石,先叔祖藝忠公妣張氏葬南屏村后山頂,此三處山每費(fèi)千元。先伯鈺亭公壽基在北山村南,計(jì)費(fèi)三千元;德璉三叔葬鴉髻嶺,土名佛仔袈裟,計(jì)費(fèi)二千元;又鴉髻山葬吳氏太婆,計(jì)費(fèi)一千元;又鴉髻山二節(jié)龍石山一處壽基,洋二千元。榮村公妣張氏葬石塘村之西爪埔,洋一千元;又自備壽基于西爪埔,約費(fèi)五百元。雨田二弟葬本鄉(xiāng)板樟山,計(jì)費(fèi)五百元。連風(fēng)水先生薪金,共用十余萬元。送用外,照簿計(jì)算,尚有九十三處窨山。(徐潤:《徐愚齋自敘年譜》,沈云龍主編:《中國近代史料叢刊續(xù)編》第五十輯,文海出版社1978年版,18-20頁)
徐潤這段文字置于同治元年暨1862年下,想必文字中“二三年內(nèi)用洋十余萬”應(yīng)是指1862年之前的“二三年內(nèi)”。還是這本年譜,咸豐八年(1858年),徐潤娶妻成家,東家寶順洋行將徐潤月薪漲至洋五十元,“俾無內(nèi)顧憂”。在此之前,徐潤的薪水是二十八元;而徐潤初入寶順洋行時(shí),“月得薪俸本洋十元”。“洋十余萬”是讓當(dāng)時(shí)作為寶順洋行買辦的徐潤無內(nèi)顧之憂的月薪“洋五十元”的兩千倍。如果徐潤的薪金不再上漲,他也不從事商業(yè)貿(mào)易,不再有其他收入,那么徐潤需要工作至少一百六十多年才能積攢下他的叔父在“二三年內(nèi)”花掉的那筆巨款。
徐潤的這位叔父就是鼎鼎有名的“世博會(huì)中國第一人”徐榮村。1851年,在英國倫敦舉行的首次世界博覽會(huì)上,徐榮村寄去“榮記湖絲”參展并獲獎(jiǎng)。這位在十九世紀(jì)中葉便具有世界眼光的中國商人,鮮為人知的另一面是“好談風(fēng)水”,短短兩三年內(nèi)便花費(fèi)十?dāng)?shù)萬巨資購買了一百多處窨山。從上文可知,徐榮村購置的一百多處“風(fēng)水寶地”,安葬了徐潤的高祖、曾伯祖、伯祖、曾祖、先祖、庶祖母等,并為在世的“先祖母容太夫人”、“先伯鈺亭公”,包括“榮村公”自己等預(yù)先選好了“壽基”所在地。其中,徐潤的曾祖父和祖父,也就是徐榮村的祖父和父親,所用“吉地”價(jià)值最為昂貴,每處均“費(fèi)二萬元”,為“全邑之冠”。值得注意的是,徐潤的高祖和曾伯祖、曾祖父等,都是安葬于徐榮村在兩三年內(nèi)所購置的風(fēng)水寶地。顯然,徐潤的這些祖輩們不太可能是在這兩三年內(nèi)紛紛去世的,而更有可能是去世多年,或已下葬而再行遷葬,或停柩不葬以待吉地而終于如愿。
停柩不葬是明清時(shí)期的中國非常普遍的一個(gè)喪葬習(xí)俗。鐘琦輯《皇朝瑣屑錄》卷三十八“風(fēng)俗”中說:“古人安葬以三月為期,江浙紳民竟有停柩至數(shù)十年之久,一家之中積至數(shù)口之多而不葬者”。乾隆年間,福建人林枝春描繪當(dāng)?shù)赝什辉岬那樾握f,停放在家里的棺材,一摞一摞的。放置在郊外的棺材,也是摞起來,像一堵堵墻一樣,到處都是。也是乾隆年間,山東掖縣知縣張思勉在《勸葬檄》中說,“(掖俗)停柩不葬,竟有遲至六七十年之久,積至三五世之多”,子孫成年,而“高曾之柩依然在堂”。就此而言,徐潤的高祖、曾祖輩先人一直停柩不葬的情況也是有可能的。停柩不葬之風(fēng)太過盛行,以至于乾隆專門發(fā)布諭旨:“朕又聞漢人多惑于堪輿之說,購求風(fēng)水,以致累年停柩,漸至子孫貧乏,數(shù)世不得舉葬。愚悖之風(fēng),至此為極。”一些以移風(fēng)易俗為己任的儒家學(xué)人建議實(shí)行“停喪不得仕進(jìn)”的政策,但最終由于實(shí)際推行的難度太大無果而終。即便這類政策曾經(jīng)在某些地區(qū)推行過,但也沒有取得多大成效。
導(dǎo)致停柩不葬的原因很多,其中一個(gè)非常重要的因素是“風(fēng)水寶地”難覓。風(fēng)水又名陰陽、堪輿、青烏術(shù)、青囊術(shù),據(jù)史料記載,先秦時(shí)期風(fēng)水觀念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到兩漢時(shí)期風(fēng)水觀念已經(jīng)運(yùn)用到實(shí)際生活中,只不過“當(dāng)時(shí)的所謂風(fēng)水主要以人的住宅即陽宅為主”。到了東漢的中后期,下葬時(shí)選擇墓地講究“風(fēng)水寶地”的觀念開始盛行,“社會(huì)上相信墓地的好壞能直接決定子孫后代的命運(yùn)”。到了魏晉南北朝時(shí)期,“一套完整的相墓、擇日以及鎮(zhèn)墓文化相結(jié)合的挑選吉穴、吉時(shí)、吉日的殯葬風(fēng)水文化體系”就正式形成了。伴隨這個(gè)過程出現(xiàn)的是一批風(fēng)水大師及其經(jīng)典著作。其中,被公認(rèn)為風(fēng)水業(yè)祖師爺?shù)墓保沁@一時(shí)期風(fēng)水界的代表人物,也正是從郭璞開始,“風(fēng)水術(shù)才真正走上系統(tǒng)化的道路”。《晉書》中有關(guān)郭璞的生平事跡中,“就有頗多關(guān)于他占卜、相墓、選址等神奇的事跡”。托名郭璞所著的《葬書》也備受推崇,成為后世殯葬風(fēng)水實(shí)踐的指南和經(jīng)典。
有學(xué)者指出,魏晉南北朝時(shí)期的風(fēng)水文化“從陽宅的營建向以殯葬風(fēng)水為核心轉(zhuǎn)移,殯葬風(fēng)水體系得到了完善”,并對后來各個(gè)歷史時(shí)期的殯葬文化產(chǎn)生了巨大而直接的影響。顯然,明清時(shí)期的停柩不葬習(xí)俗,正是殯葬風(fēng)水觀念帶來的直接后果。從“陽宅風(fēng)水”到“陰宅風(fēng)水”的轉(zhuǎn)變,背后體現(xiàn)的是古代中國“靈魂不滅”、“天人感應(yīng)”的思想觀念。“事死如事生”的傳統(tǒng)殯葬理念體現(xiàn)的也是古人對于人死后“靈魂不滅”觀念的信仰。“陰宅風(fēng)水”的流行,則表明古人不僅相信“靈魂不滅”,還相信陰陽之間存在著某種神秘的溝通渠道,祖先的“陰宅風(fēng)水”是否好,直接決定了子孫后代的命運(yùn)。有了如此關(guān)鍵的利害關(guān)系,人們不惜花費(fèi)無數(shù)金錢,寧愿等上數(shù)十年、幾代人,也要為祖先覓得一塊“風(fēng)水寶地”的做法,就變得完全可以理解了。
對今人而言,“靈魂不滅”“陰宅風(fēng)水”等觀念,顯得有點(diǎn)荒誕不經(jīng),都應(yīng)該歸入“迷信”一類。吊詭的是,死亡也成為當(dāng)今人們最被忌諱的一個(gè)話題或字眼。就像雷蒙德·穆迪在其經(jīng)典著作《死后的世界:生命不息》一書中所說的那樣,“死亡是個(gè)禁忌話題,或許我們只是下意識(shí)地覺得和死亡有任何接觸,即使是間接的,都會(huì)想到自己終究要死,從而感覺死亡近在咫尺”,“在心理層面上,人們也將談?wù)撍劳鲆暈殚g接地接觸它。許多人覺得,談到死亡無異于在心里召喚它、讓死亡現(xiàn)前,并且不得不面對自己難逃一死的事實(shí)”。顯然,是人們內(nèi)心對死亡最深沉的恐懼,讓“死亡”成為現(xiàn)代人最忌諱的字眼和話題。一位西方醫(yī)學(xué)學(xué)者指出,“盡管數(shù)萬年來,人類都接受死亡是生命的一個(gè)自然部分,但是在二十世紀(jì)初,我們對死亡的態(tài)度卻爆發(fā)過一場血腥革命。死亡成了不自然的、骯臟的、用醫(yī)學(xué)手段處理的,而且不能讓大眾看到的事情。十九世紀(jì)八十年代,大部分人都在家中去世;到了二十世紀(jì)中葉,大多數(shù)人是死在醫(yī)院里”。雖然晚了數(shù)十年,但中國顯然也經(jīng)歷了這樣一個(gè)過程。可以說,現(xiàn)代人對“死亡”的忌諱,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這樣一個(gè)過程造成的。

《死后的世界:生命不息》
再回到停柩不葬這個(gè)話題,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傳統(tǒng)時(shí)代的日常世界營造出了一種生死相依、活著和死亡密切交融在一起的生活氛圍。所停之柩,有放在家里的,也有“浮厝于野”的。相對而言,富裕家庭“房多屋廣”,“停柩于家”的情況更多一些。據(jù)乾隆《鄉(xiāng)寧縣志》載,當(dāng)?shù)厥苛?xí),視葬親為不急之務(wù),“過盡七后,將棺移置堂角,用門隔裝成一小室,或用字畫為飾,而客位中設(shè)筵會(huì)親友,恬不知怪,遂至有十?dāng)?shù)年不葬者”。張思勉在《勸葬檄》中也有類似表述:“夫陰陽道隔,人鬼殊途。以死人之棺而居生人之室,不惟先靈暴露,陰鬼不免夜號,亦且火燭堪虞,倉猝何能措手!即不以不祥為慮,亦無意外之災(zāi),而歷年既久,遇有喜慶,祖父母父母之柩塊處中堂,子若孫居然宴會(huì)婚配不疑。”很多寡婦會(huì)將夫柩置于臥室,朝夕相伴,或“紡車織具并置柩側(cè)”,“倦即依夫柩旁少息”,吃飯時(shí)則“置飯一盂柩前”。有的孤兒寡母過著守柩生活,寡母日夜坐在柩旁紡織,孤兒則偎在身邊讀書。如果小孩犯錯(cuò),屢教不改,母親則讓小孩跪在靈柩旁,進(jìn)行教育。很多“孝子傳”的記述也主要是圍繞親柩展開,孝子或“夜臥柩側(cè)”,或“出告返面,畢恭畢敬”,就像父母親還在世一樣。
如果說這種“守柩生活”過于詭異,可能只是“孝子”、“貞婦”或一些癡迷于風(fēng)水的家庭或家族所為,那么在家中設(shè)立祖先或亡人牌位,按時(shí)祭祀,恐怕就是一種非常普遍的行為了。尤其是在富裕家族乃至家庭,還可能設(shè)立專門的祠堂,以供不時(shí)之祭。以晚清帝師翁同龢為例,來看看他在光緒八年(1882年)的日常祭祀生活。正月初一日,“于真容前叩頭,合家行禮”。所謂“真容”,即翁同龢祖父母、父母之遺像,一般在除夕前夜懸掛,正月初六日“敬收”,被翁同龢稱為“此吾家舊規(guī)矩也”。光緒八年不同以往,直到正月十五日上元節(jié),翁同龢還帶領(lǐng)全家在真容前行禮,供元宵以祭祀祖先,到正月十六日,“晨敬收真容”。光緒八年的清明節(jié)是二月十八日,翁同龢因?yàn)橐M(jìn)宮教光緒帝讀書,因而在二月十七日即“清明前一日設(shè)奠祀先”。三月十八日乃翁同龢亡妻忌日,翁同龢在日記中寫道:“余未親奠也。”應(yīng)該是由其家中侄孫被代為祭奠。此前,翁同龢多是親自祭奠。同治二年(1863年)五月四日,翁妻逝世已五年,翁同龢到報(bào)國寺“相視亡妻厝室”,并感嘆“不到者半年余矣”。翁妻去世后一直停靈于報(bào)國寺,直至十年后的同治七年(1868年),翁同龢才將其父翁心存、三兄翁同書及其妻子的靈柩一并運(yùn)回原籍安葬。
四月五日,乃翁同龢“先祖潛虛公誕日”,“晨起祠堂叩頭,午奠竟未歸”;四月十四日,先祖忌日,“早晨祠堂叩頭”。四月二十七日是翁同龢的生日,“早晨祠堂叩頭”,當(dāng)其父母均在世時(shí),則是在父母親前行禮。五月五日端午節(jié),“午后奠祀先”。五月十四日,是翁同龢之父翁心存的誕日,也是翁同龢?biāo)米游淘驳募扇眨淘谌沼浿袑懙溃骸笆侨瘴绲炀乖趦?nèi)未能歸,此意可知矣,凄惻。”六月九日是翁同龢三兄翁同書的誕日,“于祠堂叩頭”。六月十三日是翁同龢“先祖母張?zhí)蛉思扇铡保霸O(shè)奠”。六月十七日是翁同龢亡妻誕日,以往一般都會(huì)設(shè)奠,有時(shí)“設(shè)奠于寢”,有時(shí)“奉經(jīng)龍泉寺”,此時(shí)只在日記中記了一筆“亡妻生忌”。六月二十五日,翁同龢的侄孫翁斌孫得子,次日翁同龢“晨起祠堂叩頭,告添丁也”。翁家一旦有此類喜事發(fā)生,翁同龢定會(huì)及時(shí)“敬告祖先”。如同治二年(1863年),翁同龢侄兒翁曾源高中狀元后,翁同龢“以曾源得大魁,具牲醴敬告祖先,于吾父神主前哭奠”。再如光緒三年(1877年),翁同龢在李鴻藻家里獲悉翁斌孫取中進(jìn)士后,當(dāng)即“馳歸告祠堂、賀三嫂,不知涕泗之橫集也”。
七月十四日,中元節(jié)前夕“申初祀先”。七月二十八日,“先祖母張?zhí)蛉苏Q日,設(shè)奠”。八月朔,乃翁同龢五兄翁同爵忌日,“設(shè)奠”。八月十五日中秋節(jié),“晨起拜祠堂,申時(shí)上祭,夜設(shè)茶供”。十月朔,“申刻設(shè)奠”。十月九日,“先祖母許太夫人忌日”,“午初祠堂行禮”。十月二十七日,翁同書忌日,“早晨行禮,午奠未親也”。翁同龢感嘆:“囊時(shí)兄亡日輒驚悸創(chuàng)楚,今乃漸忘,嗚呼,孝弟衰矣。”十月二十八日,“先祖母許太夫人誕日,未克躬奠,斌孫將事”。十一月朔,“五嫂楊夫人誕日,設(shè)奠”。十一月七日,翁心存忌日,“設(shè)奠長慟,茹素一日”。十一月十二日,冬至前夕,“吾吳所謂冬至夜也”,“傍晚供祠堂及亡室子侄孫,蓋冬至夜之祭也”。十二月二十三日,“馳歸設(shè)奠,母生日也”;十二月二十四日,“馳歸設(shè)奠,母亡日,感慟何極”。十二月二十九日,“申酉間真容前上祭,合家行禮”;十二月三十日除夕,“在真容前行禮”,“檢點(diǎn)身心”。
由上可知,翁同龢每年會(huì)固定在其祖父母、父母、兄嫂、妻兒等亡人的“誕日”和“忌日”設(shè)奠行禮,如有遺忘缺失,則在日記中予以追記并表達(dá)愧疚之意。在正月十五日上元節(jié)、清明節(jié)、端午節(jié)、七月十五日中元節(jié)、八月十五日中秋節(jié)、十月朔、冬至夜、除夕等節(jié)日,翁同龢還會(huì)率領(lǐng)家人對家中亡者進(jìn)行共同祭奠。每逢家族中有喜事發(fā)生,如添丁、取進(jìn)士、中狀元等,都會(huì)第一時(shí)間“敬告祖先”。甚至翁同龢的生日,也要像父母親在世一樣,前往祠堂叩頭行禮。可以說,在翁同龢的日常家庭生活里,“亡人”和生者緊密相依,死亡并沒有將其父母、兄長、妻兒從他身邊徹底奪走。這些“亡人”通過翁同龢年復(fù)一年、無厭其煩地祭奠,一直生活在他的身邊。

翁同龢
在這樣一種生與死幾乎完全交融在一起的生活氛圍中,死亡對于翁同龢而言,顯然不是一件多么令人的恐懼的事情。翁心存去世十年時(shí),翁同龢在其忌日哭奠,感嘆:“音容未渺,倏已十年,又罹酷罰,至于斯極,何日得侍泉臺(tái),一訴苦痛,嗚呼。”所謂“又罹酷罰”當(dāng)時(shí)指翁同龢的母親一年前去世。光緒四年(1878年),翁同龢?biāo)米游淘踩ナ喇?dāng)年的除夕前夜,翁同龢在日記中寫道:“夜祀先,悲不能收矣,人生到此亦復(fù)何意。”光緒七年(1881年)四月二十七日,翁同龢生日,“叩謁祠下,念此身煢獨(dú),旦暮填溝壑,但求少作孽,庶幾見先人于地下,他非所宜計(jì)也”。此時(shí)的翁同龢應(yīng)該沒有料到,來年(1882年)他就將入軍機(jī),得大用,以后還會(huì)經(jīng)歷乃至主導(dǎo)諸多大事,直至戊戌年被開缺回籍。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除夕,經(jīng)歷了眾多人生無常、世事變幻的翁同龢在日記中寫道:“剪燈默坐,如枯禪,如旅客。”在翁同龢而言,生死已然看淡。
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七中有一條目,名曰“士大夫晚年之學(xué)”,指“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學(xué)佛,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學(xué)仙”。身處晚年,距離死亡越來越近,而且無人可以逃避,心中的恐懼難免日盛一日。無論是“學(xué)佛”,還是“學(xué)仙”,所求都不過是強(qiáng)化自己內(nèi)心“靈魂不滅”的觀念,以緩解“大限”終將到來的焦慮和恐懼。這表明,盡管我們常說“靈魂不滅”的觀念在傳統(tǒng)社會(huì)相當(dāng)普及,但真正堅(jiān)定不移的信仰者究竟有多少,其實(shí)是很可疑的。恐怕大多數(shù)人都只是半信半疑的狀態(tài),畢竟人們都生活在物質(zhì)化的現(xiàn)實(shí)世界中,那些“怪力亂神”之事親眼目睹者少之又少,大多的信源都只是“道聽途說”。在半信半疑中,人們還是愿意花費(fèi)巨資購求“風(fēng)水寶地”,還是愿意花費(fèi)大量的時(shí)間和精力年復(fù)一年地重復(fù)著那些日常祭祀行為,這不僅是出于人們情感上的需求,同時(shí)也是人們內(nèi)心深處對于終將到來的死亡的巨大恐懼的撫慰和消解。在傳統(tǒng)社會(huì)這樣一種生和死密切交融在一起的日常生活氛圍里,死亡是一件再自然不過的事情,那么當(dāng)一個(gè)活著的人面臨死亡的時(shí)候,也許就會(huì)更從容一些吧。
(本文寫作參考了張傳勇:《清代“停喪不得仕進(jìn)”論探析——兼及清代國家治理“停喪不葬”問題的對策》,《中國社會(huì)歷史評論》第十卷;陳華文、陳淑君:《中國殯葬史》第三卷“魏晉南北朝”;余新忠、張傳勇等:《中國殯葬史》第七卷“明清”,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17年;陳義杰整理:《翁同龢日記》,中華書局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