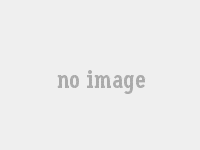商鋪門面向西必?cái)。控?cái)神爺開示:寅時(shí)調(diào)整可引八方財(cái)星!
暮春的西街總帶著股說不清的蕭瑟。陳軒度的綢緞鋪檐角銅鈴被穿堂風(fēng)卷得亂響,夕陽把朱紅門板照得發(fā)燙,木紋里滲著暖意,卻映不出半個(gè)顧客的身影。貨架上的綢緞本是上好的料子 —— 杭綢泛著珍珠母般的柔光,蘇繡綴著細(xì)如蚊足的纏枝蓮,可經(jīng)連日西曬,色澤暗了大半,像被抽走了精氣神的美人,蔫蔫地垂著,連絲線都失了韌勁。
巷口老槐樹下,鄰人們聚在青石板上搖扇閑談,聲音裹著風(fēng)溜進(jìn)鋪內(nèi)。賣針線的張嬸嗓門最亮:“都說西向商鋪留不住財(cái),陳家郎君偏不信邪!這鋪?zhàn)娱_了半年,我瞧著他從月初到月末,賬本上的赤字就沒斷過,再撐些日子,怕是要把祖?zhèn)鞯睦险佳荷蠂D。”隔壁饅頭鋪的王屠戶接話,手里的蒲扇拍得 “啪啪” 響:“可不是嘛!夏日西曬能把人烤脫皮,誰愿站在這兒選綢緞?冬日更糟,西北風(fēng)順著門縫往里灌,客人剛進(jìn)門就凍得縮脖子,哪還有心思挑料子?這地方,神仙來了也難救!”
陳軒度攥著賬本的手微微發(fā)顫,指尖按在 “三月虧損紋銀五十兩” 的字跡上,指腹泛白。忽然,檐角銅鈴無風(fēng)自鳴,鈴聲清脆得不像凡響,帶著股清冽的穿透力,壓過了巷口的閑談。他抬頭望去,暮色里似有個(gè)青布長(zhǎng)衫的模糊身影在巷口一閃而過,空氣中留下淡淡的檀香 —— 不是寺廟里的沉水香,也不是婦人用的熏香,清潤(rùn)中帶著些草木氣,與西街的煙火氣截然不同。

陳軒度的綢緞鋪開在西街中段,青磚墻黛瓦檐,原是前清時(shí)一位鹽商的鋪面,去年冬天他用祖?zhèn)鞯奈迨畠杉y銀盤下來時(shí),心里滿是憧憬。鋪面三間開闊,雕花木窗上刻著 “松鶴延年” 的紋樣,窗欞間還嵌著細(xì)紗,擋灰又透光,本該是個(gè)聚客的好地方,可自打正月十五開門,就沒熱鬧過。
“郎君,今日又只賣了半匹素綢,還是給巷尾李婆婆做孝布用的。” 伙計(jì)阿福耷拉著腦袋進(jìn)來,手里的算盤珠子撥得稀爛,算珠碰撞聲都透著喪氣。他見陳軒度盯著賬本出神,手指在賬頁上反復(fù)摩挲,忍不住小聲補(bǔ)充:“對(duì)門王記布莊今早又雇了兩個(gè)伙計(jì),我路過時(shí)瞧見,他們鋪?zhàn)永锒阎畮灼バ碌降脑棋\,聽說是江南織造局的貨,客人都排著隊(duì)預(yù)定呢。”
陳軒度揉了揉發(fā)緊的眉心,抬頭打量自家鋪?zhàn)印N绾蟮年柟庑毙鼻羞M(jìn)門框,在青磚地上投下一道分明的光影,靠近門的那排貨架被曬得發(fā)燙,他伸手摸了摸一匹湖藍(lán)色杭綢,指尖傳來灼熱感,布料邊緣的絲線已有些發(fā)脆 —— 這匹綢子上個(gè)月剛到,本是他特意托人從杭州運(yùn)來的,如今卻成了 “燙手貨”。
“把西邊的窗都掛上竹簾吧,選最密的那種,能擋些日曬。” 他嘆了口氣,聲音里帶著難掩的疲憊。阿福應(yīng)聲去后院取竹簾,竹片碰撞聲 “嘩啦” 響,穿過鋪內(nèi)的穿堂風(fēng),竟有了些蕭瑟的意味。
掛簾時(shí),阿福忍不住回頭問:“郎君,您說咱這鋪?zhàn)樱嫦駨埬窘痴f的那樣,犯了‘西曬煞’留不住財(cái)氣?” 張木匠是西街有名的手藝人,上個(gè)月來修窗欞時(shí),見鋪?zhàn)游飨颍蛣襁^陳軒度改改門向,說 “西為金,火煉金則氣燥,人躁則財(cái)散”。
陳軒度沒接話,只是指尖在賬本上劃過一個(gè)個(gè)赤字。他想起父親臨終前的話:“咱陳家雖不是大富大貴,卻也守著綢緞生意三代了,你要記住,做生意靠的是誠(chéng)信,不是旁門左道。” 可如今,誠(chéng)信撐不起虧損的賬本,父親留下的道理,在西街的西曬里,顯得格外無力。

入夏后,西曬愈發(fā)厲害。正午時(shí)分,鋪?zhàn)永锵駛€(gè)密不透風(fēng)的蒸籠,青磚地被曬得發(fā)燙,踩上去像踩在暖爐上。陳軒度只得讓阿福在門口擺了個(gè)涼茶攤,竹桶里盛著冰鎮(zhèn)的綠豆湯,杯沿搭著薄荷葉,盼著能引些客人進(jìn)門。可路過的行人都腳步匆匆,手里的扇子搖得飛快,寧愿繞到東街走陰涼路,也不愿在西曬地里多待片刻。
七月十二那天午后,熱浪裹著塵土卷過西街,陳軒度正用帕子擦汗,忽然聽見熟悉的笑聲 —— 是熟客李掌柜。李掌柜開的茶葉鋪在東街拐角,門朝東南,每日晨光先照進(jìn)鋪?zhàn)樱饧t火得很,常來陳軒度這兒買綢緞做茶包襯布。
“軒度兄,近來可好?” 李掌柜搖著把象牙骨扇走進(jìn)來,扇面上畫著水墨山水,一進(jìn)門就直擺手,“好家伙,你這鋪?zhàn)颖任夷遣枞~灶還熱!快給我倒杯涼茶,不然我這老骨頭要化在這兒了。”
陳軒度忙遞過涼茶,笑著讓座:“李兄取笑了,這鬼天氣,連風(fēng)都是熱的,客人哪肯上門?” 他引李掌柜到東邊貨架旁 —— 那里靠著后墻,能擋些日曬,“您來瞧瞧這匹蘇繡,上周剛到的新貨,繡的是‘歲寒三友’,用來做茶簾正好。”
李掌柜卻沒看綢緞,反而背著手打量起鋪?zhàn)痈窬帧K[著眼,從門楣看到后墻,又蹲下身摸了摸青磚地,眉頭漸漸皺起來:“軒度兄,不是我多嘴,你這門向確實(shí)犯忌。風(fēng)水里說‘西為兌卦,屬金,主肅殺之氣’,商鋪講究的是生氣流通,人來人往才聚財(cái),哪經(jīng)得起這般煞氣?”
陳軒度握著茶杯的手頓了頓,他雖不信風(fēng)水,卻也想聽聽緣由:“李兄這話,愿聞其詳。”
“你看東街那些旺鋪,” 李掌柜指著巷口方向,“王記糧鋪、趙記胭脂鋪,哪個(gè)不是坐北朝南?就算是朝東的鋪?zhàn)樱材苡抗饧{生氣。晨光屬木,木能生財(cái),這是老祖宗傳下來的道理。” 他又指了指陳軒度的鋪?zhàn)樱澳氵@西向,夏日火煉金,人躁則失智,客人容易挑三揀四;冬日金生水,寒風(fēng)貫戶,人冷則心散,留不住客。長(zhǎng)此以往,生意哪能好?”
李掌柜喝了口涼茶,繼續(xù)道:“我當(dāng)初選茶葉鋪時(shí),特意請(qǐng)了風(fēng)水先生看。先生說‘商鋪忌孤陽、忌沖煞’,你這西曬就是孤陽煞,再不想辦法,怕是要把家底賠光。” 陳軒度看著李掌柜認(rèn)真的神情,心里第一次泛起動(dòng)搖 —— 父親說做生意靠誠(chéng)信,可若連客人都留不住,誠(chéng)信又能給誰看?

李掌柜走后,陳軒度心里像堵了塊熱石頭,悶得發(fā)慌。他本是讀書人,年輕時(shí)還考過秀才,向來不信鬼神之說,可半年來生意慘淡,賬上的銀子日漸減少,由不得他不多想。傍晚關(guān)鋪時(shí),巷口的議論聲又飄了過來,比正午時(shí)更熱鬧。
賣豆腐的劉老栓嗓門粗:“陳家郎君太犟!王屠戶前陣子就說了,這鋪?zhàn)訐Q了三任主人,個(gè)個(gè)賠本!第一任是賣瓷器的張老板,光緒二十三年開的店,不到半年,瓷器被西曬裂了大半,賠得典了老婆的首飾;第二任是賣茶葉的周掌柜,去年來的,冬日里寒風(fēng)把茶葉吹得發(fā)潮,客人買了一次就不來了,開春就卷鋪蓋走了!”
張嬸接話,手里的針線活沒停:“可不是嘛!西街西頭那幾家,哪個(gè)不是撐不過一年?南頭的雜貨店,去年冬天還掛著‘大酬賓’的幌子,今年開春就貼了‘轉(zhuǎn)讓’的紙條;北頭的鞋鋪,老板倒是硬撐了一年,最后還是把鋪?zhàn)颖P給了東街的布商,自己回老家種地去了。”
阿福聽得氣鼓鼓的,擼起袖子就要去理論:“這群人吃飽了沒事干!咱鋪?zhàn)雍貌缓茫P(guān)他們屁事!” 陳軒度連忙拉住他,搖了搖頭:“嘴長(zhǎng)在別人身上,隨他們說去。” 話雖如此,心里卻泛起嘀咕 —— 西街西向的鋪面,換手率確實(shí)高得反常,難道真有什么講究?
回到后宅,妻子林氏正對(duì)著賬本發(fā)愁。林氏是書香門第出身,嫁過來時(shí)帶了不少陪嫁,如今卻跟著陳軒度受苦。她見陳軒度進(jìn)門,把算盤推過來,聲音帶著些哽咽:“夫君,下月房租該交了,是紋銀八兩。賬上只剩五兩了,再這樣下去,只能把我陪嫁的那對(duì)銀鐲子當(dāng)了。”
陳軒度看著妻子憔悴的臉,眼下的青黑遮不住,原本光滑的手因?yàn)檫B日算賬,指腹磨出了薄繭。他喉頭有些發(fā)緊,伸手握住林氏的手:“別擔(dān)心,我再想想辦法,實(shí)在不行,就去跟岳父借些銀子周轉(zhuǎn)。” 林氏點(diǎn)點(diǎn)頭,靠在他肩上,輕聲道:“夫君,要不咱也請(qǐng)個(gè)風(fēng)水先生看看?就算沒用,也求個(gè)心安。”

那晚,陳軒度翻來覆去睡不著。林氏的話,李掌柜的提醒,鄉(xiāng)鄰的議論,像一團(tuán)亂麻纏在腦子里。天快亮?xí)r,他忽然有了個(gè)主意 —— 與其聽別人說,不如自己做個(gè)試驗(yàn),看看西向到底對(duì)鋪?zhàn)佑惺裁从绊憽?/span>
第二天一早,陳軒度找出兩匹一模一樣的素色杭綢,都是父親留下的老料子,質(zhì)地、色澤毫無差別。他讓阿福把一匹掛在西邊貨架,正對(duì)著西曬的陽光;另一匹掛在東邊貨架,靠著后墻。又找了兩個(gè)相同的白瓷碗,各盛了半碗清水,分別放在兩匹綢緞旁,打算每日記錄變化。
接下來的半個(gè)月,陳軒度每天清晨、正午、傍晚各記錄一次。他發(fā)現(xiàn),西邊的綢緞變化格外明顯:清晨時(shí)還透著柔光,正午被曬過后,色澤就暗了一分;傍晚再看,邊緣的絲線已有些發(fā)脆,用手輕輕一扯,竟斷了兩根。而東邊的綢緞,半個(gè)月過去,依舊鮮亮如初,絲線韌勁十足。
更奇怪的是,西曬最烈的正午,鋪?zhàn)永锟倧浡还山乖甑臍庀ⅰ0⒏K阗~時(shí)頻頻出錯(cuò),原本熟練的算盤,竟能把 “三兩二錢” 算成 “五兩一錢”;陳軒度自己也覺得心煩,客人稍挑些毛病,他就忍不住想辯解,好幾次差點(diǎn)跟客人吵起來 —— 這在以前,是絕不可能發(fā)生的。
七月廿九那天晌午,熱浪裹著塵土卷進(jìn)鋪?zhàn)樱愜幎纫姲⒏E吭诠衽_(tái)上打盹,頭一點(diǎn)一點(diǎn)的,口水都快流到賬本上。他走過去拍了拍阿福的肩膀,忍不住問:“阿福,你覺不覺得午后特別容易犯困?”
阿福揉揉眼睛,打了個(gè)哈欠:“是啊郎君!我總覺得頭暈乎乎的,像被什么東西壓著似的。對(duì)門王記布莊就不一樣,我昨天路過,見他們鋪?zhàn)永餂隹斓煤埽镉?jì)們都精神著呢 —— 他們朝東,上午曬得著,下午就蔭涼了,哪像咱這兒,午后跟烤爐似的。”
陳軒度走到門口張望,對(duì)門王記布莊門朝東南,此時(shí)正有幾位婦人在挑選布料,笑語聲隱約傳來。他仔細(xì)觀察,兩家鋪?zhàn)拥拈T階高度相似,都是三寸;街道走向也一致,都是東西向;甚至連鋪面大小,都是三間 —— 唯一的不同,就是朝向。
當(dāng)晚,陳軒度翻出父親留下的舊書。書架最底層,有本泛黃的《宅經(jīng)》,是祖父年輕時(shí)手抄的,封皮上寫著 “陰陽相得,福吉始生”。他翻開書頁,在 “商鋪篇” 里看到一行小字:“凡商鋪忌西向,夏火炎上則氣躁,人躁則失客;冬風(fēng)貫戶則財(cái)散,風(fēng)散則失利。金旺克木,木為財(cái),故西向商鋪多不聚財(cái)。”
看到 “金旺克木,木為財(cái)” 七個(gè)字,陳軒度心頭猛地一沉 —— 李掌柜說的 “晨光屬木,木能生財(cái)”,竟與《宅經(jīng)》里的記載不謀而合。難道父親生前不信的風(fēng)水,真的能決定商鋪的興衰?

自那以后,陳軒度眼里處處是 “兇兆”。西曬的日光不再是尋常的陽光,成了 “煞光”,照在綢緞上像在吸走料子的靈氣;穿堂的風(fēng)聲不再是尋常的風(fēng)聲,成了 “破財(cái)聲”,吹過柜臺(tái)像在卷走賬上的銀子;連檐角的銅鈴,響聲都變得刺耳,不像以前那般清脆。
他開始失眠。每到深夜,總能聽見鋪?zhàn)永飩鱽?“沙沙” 聲,像是綢緞在被風(fēng)吹動(dòng),可后宅的窗明明關(guān)得嚴(yán)實(shí)。閉上眼睛,就會(huì)夢(mèng)見鋪?zhàn)永锏木I緞變成枯葉,被西風(fēng)吹得漫天飛舞,父親站在漫天枯葉里,眉頭皺得緊緊的,卻不說話;有時(shí)又夢(mèng)見自己站在空蕩蕩的鋪?zhàn)永铮~本上的赤字變成紅色的火焰,燒得他手忙腳亂。
林氏見他日漸消瘦,眼窩深陷,顴骨都凸了出來,心疼得很。八月初三那天清晨,她給陳軒度端來一碗蓮子羹,輕聲勸道:“夫君,你近來氣色越來越差,不如歇幾日吧?我回娘家問問岳父,他老人家讀的書多,或許認(rèn)識(shí)懂風(fēng)水的先生。”
陳軒度本想拒絕 —— 他還是覺得風(fēng)水是旁門左道,可看著賬本上的赤字,看著林氏憔悴的臉,終究點(diǎn)了頭。岳父是退休的老秀才,在縣里教過書,平日里喜歡研究陰陽五行,家里藏了不少這類書籍,或許真有辦法。
林氏第二天一早就回了娘家,傍晚才回來,手里攥著一張字條。字條是岳父親筆寫的,字跡潦草卻力透紙背:“西屬金,金旺則克木,木為財(cái);寅屬木,寅時(shí)為木氣最盛之時(shí),可通關(guān)金克木之局。然具體調(diào)整之法,需尋懂局之人,非紙上文字可解。”
林氏坐在陳軒度身邊,解釋道:“岳父說,西方在五行里屬金,金太旺就會(huì)克制木,而木代表財(cái)氣,所以西向商鋪留不住財(cái)。寅時(shí)是凌晨三點(diǎn)到五點(diǎn),屬木,木氣最盛,正好能化解西方的金氣,讓財(cái)氣流通。只是該怎么調(diào)整,他也說不準(zhǔn),只說要‘順時(shí)借氣’。”
陳軒度捏著字條,指尖傳來紙張的粗糙感。岳父的話,與《宅經(jīng)》的記載、李掌柜的提醒相互印證,他心里第一次生出嘗試的念頭 —— 或許,真該試試調(diào)整風(fēng)水?可 “順時(shí)借氣” 四個(gè)字,像個(gè)謎題,他不知道該從何下手。

陳軒度把字條折好放進(jìn)懷里,起身走到窗邊。月光透過窗欞灑進(jìn)來,在地上投下斑駁的光影,巷口傳來更夫打更的聲音 —— 已是子時(shí)了。他想起白天阿福說的話,王記布莊又進(jìn)了一批新云錦,客人排著隊(duì)預(yù)定;想起張嬸的議論,說他再撐不住就要典老宅;想起林氏哽咽的聲音,說要當(dāng)陪嫁的銀鐲子。
忽然,他摸到懷里的一樣?xùn)|西 —— 是白天整理父親舊物時(shí)找到的一枚桃木牌,巴掌大小,上面刻著模糊的紋路,像是個(gè) “財(cái)” 字。桃木屬木,寅時(shí)也屬木,這兩者之間,會(huì)不會(huì)有聯(lián)系?寅時(shí)調(diào)整,究竟該調(diào)整什么?是改門向,還是擺物件?“順時(shí)借氣”,又該借哪股氣?這些疑問像潮水般涌上來,讓他心頭劇跳 —— 若找不到答案,他的綢緞鋪,真的要撐不下去了嗎?
八月初五那天上午,西街的熱浪比往常更甚,鋪?zhàn)永镞B個(gè)避雨的客人都沒有。陳軒度正趴在柜臺(tái)上整理賬本,忽然聽見門口傳來 “吱呀” 一聲 —— 有人推門進(jìn)來了。
他抬頭望去,只見一位老者站在門口。老者身著青布長(zhǎng)衫,布料雖舊卻漿洗得干凈,領(lǐng)口袖口都縫補(bǔ)過,卻整整齊齊;須發(fā)皆白,用一根木簪綰著,垂在肩頭;手里拄著根桃木拐杖,杖身泛著溫潤(rùn)的包漿,一看就是用了多年;臉上布滿皺紋,卻精神矍鑠,尤其是那雙眼睛,炯炯有神,像能看透人心似的。
老者進(jìn)門時(shí),一股淡淡的檀香飄了進(jìn)來 —— 與那日檐角銅鈴響時(shí)聞到的氣味一模一樣!陳軒度心里一動(dòng),連忙起身迎客:“老先生,您想買些什么綢緞?”
老者沒急著回答,而是背著手,慢慢打量鋪內(nèi)。他從東邊貨架看到西邊貨架,目光在那匹褪色的杭綢上停了停,又掃過柜臺(tái)、門楣,最后落在陳軒度懷里露出的桃木牌上 —— 那桃木牌是陳軒度早上隨手揣在懷里的,此刻正露著一角。
“掌柜的,可有適合做壽衣的料子?” 老者終于開口,聲音沙啞卻有力,像老松木摩擦的聲音。他的目光重新落在陳軒度身上,帶著些探究的意味。
陳軒度連忙引他到東邊貨架:“老先生,西邊的料子被西曬得脆了,做壽衣不結(jié)實(shí)。您看看這匹云錦,質(zhì)地厚實(shí),顏色是正紅色,做壽衣最合適不過,而且耐存放,不會(huì)輕易褪色。”
老者卻搖頭,徑直走到西邊貨架,伸手拿起那匹褪色的杭綢。他用指腹輕輕撫摸布料,動(dòng)作輕柔,像在撫摸珍貴的寶物:“就它了。老朽活了八十歲,就愛這日曬后的溫潤(rùn)感 —— 料子曬過之后,少了些火氣,多了些平和,正合老朽的心境。”
陳軒度有些驚訝 —— 這匹杭綢已經(jīng)褪色發(fā)脆,他本想折價(jià)處理,沒想到老者竟會(huì)選中它。他連忙說:“老先生,這料子確實(shí)不太結(jié)實(shí),您再考慮考慮?”
“不用考慮。” 老者從袖袋里掏出一塊碎銀子,放在柜臺(tái)上,“這料子,夠不夠?” 陳軒度一看,碎銀子足有二兩,而這匹杭綢最多值五錢。他剛想推辭,老者卻擺手:“多的銀子,算老朽給掌柜的‘問路錢’。”
付款時(shí),老者從懷里掏出一枚桃木令牌,遞給陳軒度。令牌比陳軒度的桃木牌大些,正面刻著 “財(cái)神令” 三個(gè)字,字跡蒼勁有力;背面是個(gè) “寅” 字,周圍刻著細(xì)小的木紋,像是某種符咒。令牌入手溫?zé)幔瑤е刹菽練狻?/span>
“掌柜的,你這鋪?zhàn)痈窬蛛m有不足,卻占著‘兌宮生財(cái)’的隱局。” 老者意味深長(zhǎng)地說,“兌宮在西方,本是金旺之地,若能借寅時(shí)木氣通關(guān),就能化煞為財(cái)。若肯在寅時(shí)稍作調(diào)整,自有轉(zhuǎn)機(jī)。”
陳軒度握著桃木令牌,想問 “兌宮生財(cái)” 是什么意思,想問 “寅時(shí)調(diào)整” 該怎么做,可還沒等他開口,老者已轉(zhuǎn)身推門而去。他連忙追出去,只見老者的身影在巷口一閃,就消失在熱浪里,只留下一句飄在風(fēng)里的話:“桃木為引,順時(shí)借氣,心誠(chéng)則靈。”

那夜,陳軒度輾轉(zhuǎn)難眠。桃木令牌被他摩挲得發(fā)亮,令牌上的 “寅” 字仿佛活了過來,在月光下泛著微光。老者的話在腦中盤旋:“兌宮生財(cái)”“寅時(shí)調(diào)整”“桃木為引”,每個(gè)字都像一把鑰匙,卻找不到對(duì)應(yīng)的鎖。
寅時(shí)三刻是凌晨四點(diǎn)左右,正是晝夜交替之時(shí),天色最暗,也是木氣最盛的時(shí)候 —— 岳父的字條上這么寫過。移門三寸,是向內(nèi)還是向外?門是松木做的,屬木,移門會(huì)不會(huì)影響木氣?木映晨光,又該用什么木?桃木?松木?還是其他木料?
“夫君,不如依言試試?” 林氏見他翻來覆去,輕聲勸道,“老者看著不像普通人,那桃木令牌也透著靈氣。就算沒用,也損失不了什么,總比坐以待斃強(qiáng)。” 她說著,從梳妝盒里找出幾樣?xùn)|西:一把桃木梳,是她嫁過來時(shí)母親給的;一個(gè)樟木箱,里面裝著她的陪嫁衣裳;還有幾根桃木簪,是以前做針線活時(shí)用的。“這些都是木物,或許能用得上。”
陳軒度看著林氏手里的桃木物件,心里漸漸有了主意。他點(diǎn)頭起身,披上外衣:“走,咱們?nèi)ヤ佔(zhàn)永锟纯础!?林氏連忙跟上,手里提著盞燈籠 —— 西街的夜路沒有路燈,只能靠燈籠照明。
深夜的西街萬籟俱寂,青石板路上泛著月光,偶爾傳來幾聲狗吠,很快又歸于平靜。鋪?zhàn)拥闹旒t門板在月光下泛著暗光,檐角的銅鈴一動(dòng)不動(dòng),沒有風(fēng),也沒有聲響。
陳軒度掏出鑰匙打開鋪門,“吱呀” 聲在夜里格外清晰。他提著燈籠走進(jìn)鋪內(nèi),燈籠的光掃過貨架、柜臺(tái)、綢緞,一切都和白天一樣,卻因?yàn)橐股嗔诵┟C穆感。他走到門口,仔細(xì)觀察門框 —— 門框是上好的松木,做了卯榫結(jié)構(gòu),門軸是黃銅的,因?yàn)橛玫镁昧耍行┌l(fā)澀。
他試著將門向內(nèi)推,“嘎吱” 一聲,門竟真的動(dòng)了。他一邊推一邊數(shù),推到三寸時(shí),門忽然卡住了 —— 正好卡在一個(gè)卯榫節(jié)點(diǎn)上,不晃也不動(dòng)。“原來如此!” 陳軒度心里一喜,“這門本就能移動(dòng),只是平時(shí)沒注意。”
林氏湊過來,燈籠光照在門上:“夫君,移門三寸,是不是就是讓門卡在這個(gè)位置?” 陳軒度點(diǎn)頭:“應(yīng)該是。你看,移門之后,門口的光影變了 —— 以前西曬能直射到東邊貨架,現(xiàn)在只能照到門口,正好避開了綢緞。”
他又想起老者說的 “木映晨光”,指著西邊窗臺(tái):“明天寅時(shí),咱們?cè)谶@兒擺上桃木物件,再放兩盆綠植,讓晨光照在上面,正好借木氣化解金煞。” 林氏連忙記下:“我明天一早就去花市買綠植,要選葉片厚實(shí)的,聽說那樣聚氣。”
兩人在鋪?zhàn)永锩β档胶蟀胍梗愜幎茸尠⒏C魅找鷷r(shí)來幫忙 —— 移門需要力氣,他一個(gè)人怕是搬不動(dòng)。月光透過窗欞灑進(jìn)來,在地上投下斑駁的光影,仿佛預(yù)示著即將到來的變化。離開鋪?zhàn)訒r(shí),陳軒度摸了摸懷里的桃木令牌,令牌依舊溫?zé)幔袷窃诨貞?yīng)他的期待。

八月初七那天,寅時(shí)三刻還沒到,陳軒度就醒了。他穿上衣服,見林氏已經(jīng)起了,正往竹籃里裝東西:桃木令牌、紅布、糯米、一把新的銅剪刀,還有昨晚準(zhǔn)備好的桃木葫蘆、木刻財(cái)神像 —— 桃木葫蘆是他連夜找木匠做的,木刻財(cái)神像是從岳父家借來的。
“都準(zhǔn)備好了?” 陳軒度問。林氏點(diǎn)頭:“都準(zhǔn)備好了,糯米是新收的,紅布是純棉的,銅剪刀是剛買的,木匠說桃木葫蘆要選老桃木,我特意讓他挑了三十年的老桃木做的。”
兩人提著竹籃出門,剛到鋪?zhàn)娱T口,就看見阿福打著哈欠走來:“郎君,林娘子,你們來得真早!我這一路上都沒見著人,就聽見雞叫了。” 阿福手里拿著撬棍,是用來移門的 —— 雖然門能移動(dòng),但需要撬棍借力。
此時(shí)的西街還浸在墨色里,東方的天空只有一絲微光,空氣里帶著露水的涼意,吹在臉上格外清醒。陳軒度打開鋪門,阿福連忙把撬棍遞過去:“郎君,移門時(shí)我來撬,您指揮就行,我力氣大!”
陳軒度握著桃木令牌,走到門后:“阿福,你把撬棍卡在門軸下面,慢慢用力,只移三寸,別多移。” 阿福點(diǎn)點(diǎn)頭,蹲下身,將撬棍卡在門軸下,“嘿” 地一聲用力,門 “嘎吱” 響了一聲,開始慢慢移動(dòng)。
“一寸…… 兩寸…… 三寸!” 陳軒度數(shù)著,到三寸時(shí)連忙喊停,“好了!卡住就行!” 阿福松開撬棍,門果然穩(wěn)穩(wěn)地卡在那里,不晃也不動(dòng)。陳軒度按照老者的囑咐,先在門軸處撒了糯米 —— 糯米在風(fēng)水里有凈宅的作用,能驅(qū)散晦氣;又用紅布擦拭門框,紅布屬火,火能生土,土能生金,卻又能制金,正好平衡西方的金氣。
剛擦完門框,東方的天空泛起魚肚白,第一縷晨光像細(xì)線一樣,從門縫隙里鉆進(jìn)來,正好落在西邊貨架上。“快,把桃木掛件掛上!” 陳軒度指揮阿福,將桃木葫蘆掛在門楣左側(cè),木刻財(cái)神像掛在右側(cè) —— 左側(cè)屬木,右側(cè)屬火,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正好形成五行循環(huán)。
林氏則將帶來的綠植擺在西邊窗臺(tái)上 —— 是兩盆綠蘿,葉片厚實(shí),藤蔓纏繞,屬木,又能凈化空氣。她一邊擺一邊說:“花市的老板說,綠蘿最能聚氣,擺在西向的窗臺(tái),正好能擋煞。”
晨光漸亮,從細(xì)線變成光束,照在桃木掛件上,泛出溫潤(rùn)的光澤;照在綠蘿葉片上,露珠折射出彩虹般的光;照在綢緞上,原本褪色的杭綢,竟也透出些柔光。陳軒度看著調(diào)整后的門面,忽然明白老者的用意:移門三寸,避開了直射的西曬,讓晨光只能照到門口,引客人進(jìn)門;桃木屬木,化解西方金煞,讓財(cái)氣流通;晨光屬木,與桃木呼應(yīng),借自然之氣補(bǔ)鋪?zhàn)又保龖?yīng)了 “木映晨光” 的說法。
他摸了摸懷里的桃木令牌,令牌比之前更熱了些,像是在確認(rèn)他的理解。阿福看著眼前的景象,忍不住感嘆:“郎君,這晨光照進(jìn)來,鋪?zhàn)雍孟窳撂枚嗔耍∫郧翱傆X得壓抑,現(xiàn)在竟覺得心里敞亮。” 林氏也點(diǎn)頭:“是啊,連空氣都覺得清新了些。”

調(diào)整后的第一日,生意并無明顯變化。鋪?zhàn)永镏粊砹艘晃豢腿耍I了一尺素綢做鞋面子,還是阿福在門口拉來的。傍晚關(guān)鋪時(shí),阿福唉聲嘆氣:“郎君,怕是白折騰了。那老者是不是騙咱們的?”
陳軒度心里也有些打鼓,可他想起老者的話,想起桃木令牌的溫?zé)幔€是強(qiáng)作鎮(zhèn)定:“再等等,岳父說風(fēng)水調(diào)整需等氣場(chǎng)流轉(zhuǎn),哪能這么快見效?” 林氏也安慰阿福:“是啊阿福,咱們?cè)俚葞兹眨f不定就有轉(zhuǎn)機(jī)了。”
第二日,依舊冷清。陳軒度卻沒放棄,他按照老者的暗示,每日寅時(shí)都來鋪?zhàn)永镎碡浖?—— 把西邊的綢緞挪到東邊,讓晨光照在上面;用濕布擦拭桃木掛件,保持桃木的溫潤(rùn);給綠蘿澆水,讓葉片始終鮮亮。他覺得,就算風(fēng)水沒用,整理鋪?zhàn)右彩呛玫模辽僮屼佔(zhàn)涌雌饋砀麧崱?/span>
第三日清晨,寅時(shí)的露水還未干,陳軒度正在整理貨架,忽然聽見門口傳來 “吱呀” 一聲 —— 有人推門進(jìn)來了!他抬頭望去,是位提著籃子的婦人,穿著藍(lán)布衣裳,籃子里裝著些針線活。
“掌柜的,早啊。” 婦人笑著走進(jìn)來,目光掃過鋪內(nèi),“我今早路過,聞著你這鋪?zhàn)永镉泄商聪悖貋砜纯础!?陳軒度驚訝地發(fā)現(xiàn),自己并未點(diǎn)香,鋪?zhàn)永镆矝]有熏香,那股檀香,正是老者身上的氣味,清潤(rùn)中帶著草木氣。
“您想買些什么綢緞?” 陳軒度連忙迎上去。婦人走到東邊貨架前,指著一匹粉色蘇繡:“這匹蘇繡真好看,繡的是‘蝶戀花’吧?我想給女兒做件嫁衣,正缺這樣的料子。” 她又指著一匹湖藍(lán)色杭綢,“這匹也不錯(cuò),做里襯正好。”
陳軒度給婦人介紹料子的質(zhì)地:“這蘇繡是江南繡娘繡的,用的是雙股絲線,耐穿不勾絲;杭綢是杭州織造的,透氣性好,夏天穿也涼快。” 婦人聽得頻頻點(diǎn)頭,最后選了兩匹蘇繡、一匹杭綢,付了五兩紋銀 —— 這是鋪?zhàn)娱_半年來,單筆最大的生意!
婦人臨走時(shí),笑著說:“掌柜的,你這鋪?zhàn)咏裨缈粗撂枚嗔耍幌褚郧澳前愠翋灐3抗庹赵诰I緞上,料子都透著光,看著就舒心。” 陳軒度這才注意到,移門后,晨光能照進(jìn)鋪?zhàn)由钐帲?qū)散了往日的陰暗,連空氣都覺得清新了些。
接下來幾日,客人漸漸多了起來。八月初十那天,來了位書生,說是要去京城趕考,想買素綢做長(zhǎng)衫,陳軒度給了他優(yōu)惠,書生說考完試還來買;八月十一,來了位商人,看中了一匹云錦,說要給母親做壽衣,一次性買了兩匹;八月十二,巷口的張嬸也來了,買了一尺紅綢給孫子做肚兜,還說 “以前覺得你這鋪?zhàn)訍灒F(xiàn)在竟覺得涼快”。
阿福忙得腳不沾地,算賬時(shí)卻再不出錯(cuò),手指在算盤上翻飛,算珠碰撞聲都透著歡快。他樂呵呵地對(duì)陳軒度說:“郎君,這寅時(shí)調(diào)整真管用!連我算賬都順了,以前總覺得頭暈,現(xiàn)在竟覺得精神得很!”
陳軒度看著日漸紅火的生意,看著賬本上的赤字慢慢減少,心里百感交集。他想起老者的話,想起岳父的字條,想起《宅經(jīng)》的記載,終于明白所謂 “風(fēng)水”,不過是順應(yīng)天時(shí)地利,讓人與環(huán)境和諧相處罷了 —— 西曬不是煞,只要避開直射,就能利用晨光;穿堂風(fēng)不是禍,只要保持流通,就能凈化空氣;桃木令牌不是神物,只是借木氣提醒人順應(yīng)自然。

中秋前夕,西街漸漸有了節(jié)日氛圍。巷口掛起了紅燈籠,各家商鋪都貼了 “中秋大酬賓” 的紙條,陳軒度的綢緞鋪,成了西街最熱鬧的地方。不僅因?yàn)樯夂棉D(zhuǎn),更因他摸索出一套 “寅時(shí)理貨” 的規(guī)矩 —— 每日寅時(shí)整理貨架,讓綢緞吸收晨光露水,色澤愈發(fā)鮮亮;用桃木梳梳理綢緞的絲線,讓料子更順滑;給綠蘿澆水時(shí),順便擦拭柜臺(tái),讓鋪?zhàn)邮冀K整潔。
九月初八那天上午,常客王夫人特意上門。王夫人是縣里富商的妻子,以前總在王記布莊買綢緞,如今卻成了陳軒度的老主顧。她一進(jìn)門就笑著說:“陳郎君,我來預(yù)定十匹云錦,要最好的料子,給我家女兒做嫁妝。”
陳軒度連忙引她到東邊貨架:“王夫人,您看看這匹云錦,是江南織造局最新的貨,繡的是‘百子圖’,顏色正,絲線密,做嫁妝最合適不過。” 王夫人伸手摸了摸,贊嘆道:“果然好料子!比王記布莊的云錦還順滑,色澤也亮些。都說你這鋪?zhàn)痈倪^風(fēng)水,連料子都沾了財(cái)氣,我看是真的!”
陳軒度笑著解釋:“王夫人說笑了,哪有什么財(cái)氣?只是每日寅時(shí)理貨,讓綢緞多吸收些晨光露水,料子自然鮮亮。再說,我這鋪?zhàn)拥牧献樱际沁x的上等貨,誠(chéng)信經(jīng)營(yíng),客人自然愿意來。”
王夫人點(diǎn)點(diǎn)頭:“話是這么說,可以前你這鋪?zhàn)永淝澹乙瞾磉^一次,總覺得悶得慌,沒選就走了。現(xiàn)在再來,竟覺得敞亮又涼快,連心情都好了。” 她又選了幾匹蘇繡、杭綢,付了二十兩紋銀,說:“我還要介紹些朋友來,你可得給我留好料子。”
陳軒度連忙應(yīng)下,送王夫人出門時(shí),正好看見巷口有個(gè)熟悉的身影 —— 是那位神秘老者!老者依舊穿著青布長(zhǎng)衫,拄著桃木拐杖,正朝鋪?zhàn)幼邅怼j愜幎冗B忙迎上去:“老先生,您怎么來了?快請(qǐng)進(jìn)!”
老者笑著點(diǎn)頭,走進(jìn)鋪?zhàn)印K蛄恐亙?nèi)的景象 —— 客人來來往往,阿福忙著招待,林氏在柜臺(tái)后算賬,貨架上的綢緞鮮亮如初,晨光透過門縫隙照進(jìn)來,落在桃木掛件上,泛著柔光。
“掌柜的悟了?” 老者捻須笑道,聲音依舊沙啞卻有力,“風(fēng)水風(fēng)水,藏風(fēng)聚氣,氣順則財(cái)生。你之前覺得西向是煞,是因?yàn)闆]找到與環(huán)境和諧相處的方式;如今移門借光,理貨順時(shí),讓人與鋪?zhàn)印⑴c自然都順了氣,生意自然就順了。說到底,還是人心順了,氣才順,財(cái)才生。”
陳軒度這才明白,老者并非什么神仙,也不是什么風(fēng)水先生,而是位懂環(huán)境智慧的隱士。他留下的 “寅時(shí)調(diào)整”,不是玄學(xué)秘法,而是順應(yīng)自然的方法 —— 寅時(shí)木氣盛,借木氣平衡金氣;晨光屬木,借晨光引生氣;桃木屬木,借桃木提醒人順應(yīng)天時(shí)。老者留下的不僅是調(diào)整方法,更是 “順應(yīng)自然、誠(chéng)信經(jīng)營(yíng)” 的道理。
他從柜臺(tái)里取出那枚桃木令牌,遞給老者:“老先生,這令牌該還給您了。” 老者卻擺手:“留著吧。它不是什么財(cái)神令,只是我用老桃木做的普通令牌,能提醒你記住順應(yīng)自然的道理,就夠了。” 說完,老者轉(zhuǎn)身推門而去,像上次一樣,消失在西街的熱鬧里,只留下淡淡的檀香。

西街的綢緞鋪依舊門朝正西,卻再無人說 “西向必?cái) 薄j愜幎葓?jiān)持著寅時(shí)理貨的習(xí)慣,不是迷信鬼神,而是遵循著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規(guī)律 —— 西曬的日光不再是 “煞光”,成了晾曬綢緞的天然條件,讓料子吸收晨光后愈發(fā)鮮亮;穿堂的風(fēng)不再是 “破財(cái)聲”,成了流通空氣的良方,讓鋪內(nèi)始終清新;檐角的銅鈴,響聲又變得清脆,常伴著客人的笑語聲,在西街的煙火氣里,格外動(dòng)聽。
人們漸漸明白,所謂風(fēng)水并非玄之又玄的迷信,而是古人總結(jié)的環(huán)境智慧 —— 順應(yīng)天時(shí),借自然之力補(bǔ)自身之缺;和諧相處,讓人、商鋪、自然形成良性循環(huán)。商鋪興衰終究靠的是誠(chéng)信經(jīng)營(yíng)與順勢(shì)而為,正如陳軒度常對(duì)客人說的:“三分風(fēng)水,七分人心。寅時(shí)的晨光再好,桃木令牌再靈,也照不亮奸商的賬本;只有誠(chéng)信待人,順應(yīng)自然,才能留住客人,留住財(cái)氣。”
那枚桃木令牌被陳軒度供奉在柜臺(tái)正中,令牌上的 “寅” 字,在晨光里泛著溫潤(rùn)的光,時(shí)刻提醒著他:順應(yīng)自然,誠(chéng)信為本,這才是商鋪長(zhǎng)久的 “財(cái)星”。西街的風(fēng)依舊吹著,卻不再是蕭瑟的風(fēng),而是帶著煙火氣的、溫暖的風(fēng),吹過綢緞鋪的檐角,銅鈴聲清脆,像在訴說著一個(gè)關(guān)于 “順應(yīng)” 與 “誠(chéng)信” 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