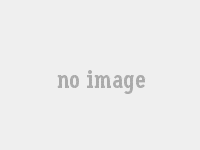全面抄襲!印度的風水學和梵天信仰,實證古印度來自中華文明
爭論沒停,關于二十八宿的起源,誰也不肯服氣。二十八宿,印度那邊叫二十七宿,數字差一個,用法差不多。真要梳理細節,哪個更古老?誰影響了誰?無數專家學者都繞著圈子爭了大半個世紀。少見有定論。網上兩個聲音此起彼伏:有的說漢傳印度,有的說印度影響中原。兩邊都有數據論證、文獻佐證,邏輯鏈條繞到腦漿沸騰還得熬夜翻資料,大家下場都像福爾摩斯。他們能找出河圖洛書,也能掏出吠陀天文。

再說個小插曲,古印度那邊對二十八宿不算陌生,學者們找到了大量古印度文獻,里面宿名宿序和中原也差不太多。只是具體怎么運用,時間上是個問題。中國史料最早追溯回殷墟甲骨文、商周青銅銘文。印度那邊,吠陀時代和摩奴法典提及恒星系統,實際應用時間稍晚。有些印度學者堅稱自家祖傳,但考古實證不全。真要比誰更早?好像都拿不出壓倒性的證據。

國內主流學界傾向于本土起源。原因多,很關鍵一點——相關符號的形態,從甲骨文、金文連到楚帛書,二十八宿叫法、排列清清楚楚,演變過程像放電影一樣能追蹤。那種“斷檔感”很低。反觀印度文獻里的宿名目錄,有拼接痕跡。歷史有趣處正在這,彼此似乎都從未單純原生,而是互相影響、融合魔改。

巧合非常多!比如有段時間,印度天文學家拜訪中國,帶走了不少天文儀器和星圖;反過來東晉以后,唐代密宗高僧也頻繁游學恒河。思來想去,沒準二十八宿本是個共享概念,經過區域濾鏡才有差異。有的學者干脆一句:沒人能說清,索性互致敬意,各取所需,各自開心。

順便一提,誰還記得上世紀對水稻起源的爭議?二十年前主流觀念還是學界普遍認同印度河流域才是最早水稻種植地。直到河姆渡遺址和上山文化中大量七八千年前的稻谷、炭化稻米出土,學者傻了眼。考古隊愣是從浙江出發,北到山東、江蘇,陸續發現栽培稻痕跡。證據一擺,印度水稻起源說不得不改口。現在國際上大都認可中國是水稻馴化中心。數據多得讓人懷疑眼睛:2016年刊《自然》雜志公布的遺傳分析,顯示亞洲稻有兩個獨立馴化中心,主源清晰可見,那傻瓜都明白誰先誰后。

這事背后,其實涉及文明大傳播。梵天,被印度奉為天地主神,造字之神,也是造書天。書籍記載里,梵天負責創世與創文,全印流行。玄妙地方在于,他同時“坐鎮”印度風水圖正中。現在印度的風水書,不,得說是feng shui,封面還直接印著漢語拼音。這細節挺刺眼。你要問,印度風水圖中央為什么是梵天?那你順手查百度,滿屏幕清一色中式羅盤、整理術語、方位十足。凡風水講究中央有一個人,打坐狀,標記正中心。梵天肚臍中央,就懟在那里,就叫黃。

一件更好玩的事,古印度所有風水羅盤外,嵌著一圈圈方位線,配著肚臍中央的梵天,中文甲骨文的黃字輪廓,就這么繞著出現。考古里常說“中央的人”,其實跟黃帝崇拜、以中為尊那套觀念,不知不覺很像。甲骨文的黃,就是人形,中間一個“田”象征肚臍,也代指黃帝、黃庭。

黃庭在道教修煉里重要得離譜。《黃庭經》講的黃庭丹法,主修“內景”,中宮養氣、丹田之術。奇怪就在于,這些技藝跟印度瑜伽術、冥想、呼吸法有驚人的相似。國內考據派說,《黃庭經》遠早于部分印度瑜伽文本,有可能是瑜伽的祖宗。但也有人堅持反過來,說誰能證明一定是中原先傳出去?抬杠幾乎無時無刻不在。

“黃”在中原的象征意義不是一天兩天了,黃帝自居天下中央,主土德,治四方。先秦時講“中央、土、黃”,以后地理、氣象、社會秩序都要圍繞“中”,制度、祭祀,連顏色都挑黃色為尊。淮南子寫得太認真了,直接說了“中央,土也,其帝黃帝,其佐后土,執繩而治四方”。

然而,印度的梵天其實對應的不就是中央四面主宰嗎?梵天相傳四面,東南西北四頭。黃帝四面像?商代青銅器上的大禾鼎,赫然一個圓滿對稱,加四方向人頭,有些青銅器放大圖,臉部輪廓和東南亞雕塑說不定都搞混。甚至更扯的,有考古家還真兩邊串聯,把古埃及的哈托爾女神(三面或四面像)都揪出來和中華黃帝像放一塊對比。你說牽強嗎?可視覺沖擊確實奇異。

古埃及那頭發現過有虞氏的甕棺葬,5500年前的。所謂甕棺,就是倒扣大陶甕,人蜷曲著埋進去,這個做法據說傳入后才逐步變成木乃伊葬法。同期印度河流域也在覺醒,出現金文、稻米、大型聚落,南亞稻米分析和東亞水稻血緣關系,專家已經追到了基因序列。“所有的文字、所有的農作、所有的葬制”都似乎有條主線,從黃帝有虞時期甩出去,一路甩到西印度、埃及。

當然,說中華一脈絕對影響世界,難免自大。歷史現場遠比我們想象復雜。有虞氏的影響力確實夠大,但南亞、西亞自身也不是泥偶。往往是你給我,我給你,變化在交鋒與嫁接之間。前一個觀點說二十八宿全是中國原創,但后一個想想又覺未必這么絕對,誰規定神話不能走個混血路線。歷史本來就不那么公正,今天學者資料堆積如山,明天又天翻地覆,規律都像流沙。要不怎么說爭論到現在也還是一頭霧水?

真實世界從未有過絕對孤立的文明。有來有往,混搭融合。二十八宿、風水、修煉、神靈形象,被塑造在一層又一層復調里頭。每次追溯溯源,線索能打個死結,概率比中彩票還高。各種最新考古報告、基因數據、銘文譯本,最近幾年又挖出一堆新遺址,不排除幾年后還有逆轉。互聯網公開信息已經把這些彼此糾纏的故事反復洗牌,就是沒有絕對蓋棺定論。

那一個甲骨文“黃”,一根稻米苗,一張古代羅盤,一尊四面神像,最終連接起了中國、印度、埃及、西亞這些老牌文明,看似熱鬧,其實更像互拍肩膀。歷史誰也獨成不了局,有時你說自己是鼻祖,轉頭又發現是別人家的晚輩。仔細想想,這種混雜與爭議,反而是真相應有的樣子!現實愈發讓人相信,最早的答案往往流動在路徑和交匯之間。

文明的路上,邊界是虛的,傳說是真,變遷是常態。誰也別急著宣布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