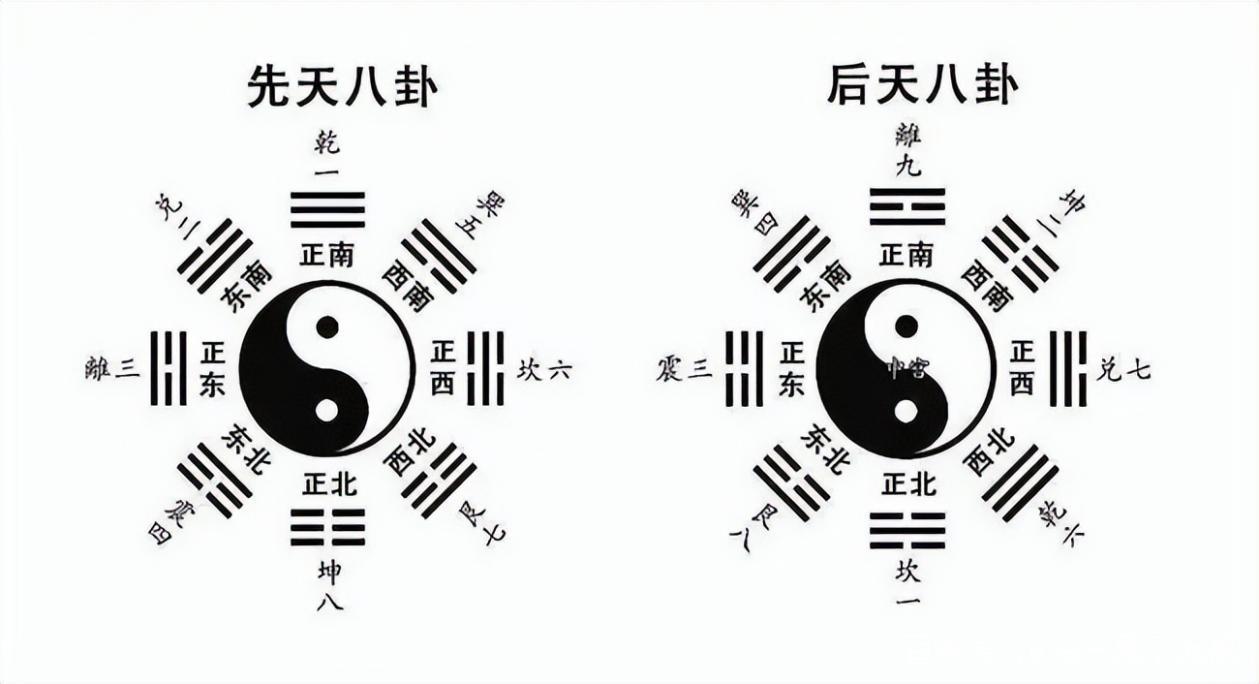在撤地設市的大潮過后,目前僅存七個地區,都位于邊境地區
那些年頭,“地區”可是個有分量的詞,現在小年輕們一提,十有八九會看你一臉懵。早些時候,飯桌上一聊到“在哪上班啊”,有人答——“地區行署”,你就知道這是正兒八經體制內的人。可現在,你再說“我在地區”,多半得補一句“哦,是大興安嶺那個地區,不是咱縣里的地區”。時代變了,這個詞在不少人的記憶里被一點點擱淺。到底是什么風水輪流轉,讓“地區”從紅紅火火到只剩七個?這事兒值得翻出來絮叨絮叨。

要說“地區”這個行政單位,吧,也沒咱們今天想得那么高大上。它雖然掛個“地級”,其實并不算咱憲法里的正式角色,說起來更像是省里的一個分店,派個人坐鎮管著下面的縣區。專員是誰,那都是省里一聲令下,直接安排,不興那些人大選舉的繁瑣。據說還不用設專門的人大政協,頂多讓上頭派來個代表小組,幫著盯盯事兒。你想想,氣氛應該很像陪老領導下鄉,總帶著點“省城來的干部”,跟地方打八竿子都拽不上。
但話又說回來,很多地方當年都設了地區,這在八十年代的中國特別普及。你家親戚湊熱鬧,逢年頭還互相打聽,“他分去哪個地區了?管幾個縣?”可到了后面,特別是九十年代,風潮一上來,“撤地設市”就儼然成了大勢所趨。不少曾經讓人仰望的地區,一夜間改頭換面,成了地級市。那些老牌“地區行署”牌子,像是超市關門時的燈——漸暗漸冷,只剩門口幾個保安還摸摸鼻子吁口氣。

要說這改革也不是憑空來的。那幾年中國人都鉆營著“現代化”,城市變大了,交通起來了,大家覺得老“地區”這攤子事太分散,行政套娃似的,反而添麻煩。撤了,合成一座市,牌子亮堂,人也好管理。可惜的是,那些曾經在地區行署里端茶送水的小青年,也像是跟著老建筑一起消失在大風里。偶爾他們跟你講起當年,也不過是一頓酸甜苦辣,帶點感慨:“那時候沒有現在這么熱鬧,但日子過得踏實。”
可有意思的是,七個“地區”硬生生地留了下來。也不是因為誰多固執,主要還是地理和民族的事兒纏著——你想黑龍江那片大興安嶺,天高地遠,林子那么大,挨個縣合起來人煙還沒一座二線城市多。這地方,給你設個市,光管理就得把人累趴下。塔城、阿勒泰什么的,更別說了,一望無際,蒙古包和胡楊林比樓房還多。管這些地兒,得靠大區抓大面,省里直接派個人過來,省得層層下傳、消息還堵在中途。

說到專員這個角色,說白了也挺尷尬。他既不是市長,也不像縣委書記,和人大政協沒啥直接關系,就是省里面的“機場代表”——隨叫隨到。許多人干了幾年,天天收集各縣的小報告,遇上民族節日,還得帶頭張羅。外人看著風光,其實壓力忒大:既要服從省里頭兒,也得讓地方服貼,像個在兩頭跑腿的中介,夾在中間說話還得分寸拿捏。深夜回家想起,或許他心里也泛酸——外地人喊他“專員”,可當地百姓還是習慣叫他“行署領導”,多少帶點兒疏離感。
再說這檢察院,地區這層又不是本院,完全是省級檢察院給安插來的。你在某個邊遠地兒,碰見檢察分院的大門,別以為能探出什么特權來,實際都是省里派下來的“臨時工”。大家習慣了也就不多問,反正只要不出大事,誰都懶得細究這些官銜。
不過別看“地區”如今剩得稀少,可各自都挺有性格。有些地方馬路兩邊,會掛著“地區行署”牌子,附近是小市場、牛肉串店、偶爾還能看到幾個穿制服的干部在吃早點。你要是耐心聽街坊聊家常,就會發現:這里的人對“地區”沒有太多崇拜。大家更關心桑塔納開到不好走的路上會不會刮底盤,或者行署大院的供暖哪天才徹底熱起來。行政區劃變來變去,生活的事,還是跟地氣掛鉤。
阿里地區,塔城地區、和田、喀什……這些名字,像地圖上的留白。始終夾在城市和自然之間,既有邊疆風,也打著民族烙印。那邊的老人一提“我們地區專員”,說話總要帶點敬意,但心里更掛念下一場棉花收成怎么樣。務實如他們,頭銜再大,不如日子過得順心。
最難管理的地兒,也往往被大浪潮遺忘、躲掉。也許,“保留”不是因為它有何權力或榮耀,而是現實逼著大家做選擇。邊境的路太遠,山太高,雪太厚,民族太雜,管理得講究方法。有時候行政架構不是型制,是妥協,是一份無奈。
我小時候,也總想弄清楚,為什么我們縣里沒有“地區行署”,而鄰省偏僻的親戚家卻有。后來才明白,行政規劃背后,既有國家的算盤,更有生活的無常。它活在地圖上,也活在每個在大院門口散步的老干部眼里。
也許某一天,“地區”會徹底消失,連同那些老馬路、灰舊宿舍樓一起變成回憶。可人們的日子還是過下去,管你是市,是縣,是地區。就像北方冬天的風,吹得門牌掉了也沒人特意彎腰拾起。真正的生活,總是在名字以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