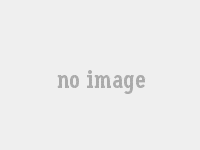河北地級市的滄州,歷史名人云云,一起看有哪些著名的歷史人物呢
來自滄州的故事,總有點不一樣。你以為每個地方都“盛產(chǎn)名人”,但仔細一琢磨,這小城邊兒上,東挨著海,北頂著天津,居然在歷史的煙塵里走出了這樣一串刻在課本、腦海、戲臺上的名字。有人寫詩,有人治病,有人舞刀弄槍,有人折騰大事。咱們今天就嘮嘮滄州那些“有名有姓”的老人物,有的風光一世,也有的,彎彎繞繞,走過好些冷冷清清的日子。

關(guān)于扁鵲這位神一樣的大夫,說起來,總讓人有點敬畏。他不是那種一出生就名氣大的角色。小時候,估計也就是村口娃里頭個子不起眼那個。可你要問他怎么就成了“醫(yī)祖”,那真不是光靠天賦。想象他穿行在戰(zhàn)國的市井,耳朵透著靈,眼睛賊亮,啥病一見就心里有數(shù)——有時候診脈,有時候干脆盯著你看好半天。不管是哪種,他總是比別人多想一步。你說這四診,望聞問切聽著簡單,可在那個時代,誰有閑工夫琢磨這些細枝末節(jié)?他就是愿意把鬧心的病、奇怪的癥都搗騰明白。
有人說扁鵲有點“怪”,他能感受到人的生死邊界,有時候病人自己都不知道,扁鵲卻已經(jīng)著急上了。他到處救人,幫了別人,可偶爾也給自個兒惹上麻煩。畢竟,哪朝哪代,手藝好的人,總有嫉妒的、誤會的,他自己也不總能擺脫那些瑣事煩惱。

說到馬致遠,那可又是另一副光景。聽說他小時候書沒少讀,但也不是那種埋頭只認字的“書呆子”。馬致遠喜歡熱鬧,偶爾混在劇場門口,看著演員你來我往,心里頭琢磨:要是我來寫,能不能寫得比這幫人還熱鬧?后來,他干脆成了寫戲的大拿。南腔北調(diào)的市井人生、酸甜苦辣的舞臺傳說——馬致遠不是只會端著架子寫文人騷情,他筆下的人物,跟咱身邊人一樣,有嘴有臉,有說有笑。你覺得他在梨園“香貫”,其實他也曾在寂寞深夜里反復修改一句歌詞,一個場面,琢磨個半宿。
但別看馬致遠在人前風風光光,他也有自己的孤單——元代不比唐宋,曲子算是新鮮玩意,老一輩的人時常搖頭,說這是“不正經(jīng)”。馬致遠愣是頂著一票質(zhì)疑,把曲子玩出新花樣,還成了“狀元”。或許他睡前會想:要不是我“活得通透”,這些曲子就像街邊的落葉,風吹雨打,誰還管呢?

再說紀昀,那人你可能印象不深——可他留下的東西,一本《四庫全書》,夠滿滿當當好幾庫房。紀曉嵐有時被說是“貧嘴”,其實他嘴皮子溜是天賦,但心里藏的,是一肚子的聰明。他混跡朝堂那么多年,看過太多世態(tài)炎涼。你想他官途有多復雜?左都御史、兵部尚書,從南到北,跑得像送快遞。雖說位高權(quán)重,紀昀更像個活得明白的人。有一次他跟皇帝頂嘴,別人捏一把汗,他卻照舊自如,心里想著:天下事,本就三分涼兩分熱,自己只管手里那點書卷和快樂就行了。
說到張之洞,這人有點像“拼命三郎”,同年中解元、進士探花,都是文人的頂點。但他家鄉(xiāng)滄州,離官場的繁華有點遠,有時候冷風過院子,張之洞或許也會想,自己是不是該安靜一陣。可人有志不在年高,他少年得志,后來一路爬升,做到了軍機大臣。在京城外頭的兩廣、湖廣、兩江——這些地方聽到他的名字,總是帶點“倔強”和“改革”的味道。他想要中國強、官場清,難,真難。有的人跟他斗,有的人跟他和,他夾在中間,既是領(lǐng)路人,也是受累人。

輪到馮國璋了,這人不同。他出身河北河間,身上總帶點北方人的倔氣。馮國璋做過教官,也統(tǒng)兵打仗。說白了,有點像那種“老經(jīng)驗”的帶隊隊長。辛亥革命那陣子,他領(lǐng)北洋軍,一邊是新世界的呼喊,一邊是老規(guī)矩的壓力。馮國璋不是文人,世事如棋他多明白點,可這個明白,一旦放進國家命運的棋盤,有時反而更難受。或許他想得最多的,其實是怎么保家、怎么保人,再怎么變,總得撐住自個兒的底線和家鄉(xiāng)的牌面。
馬本齋的名字,在抗戰(zhàn)那幾年,滄州人誰不心疼。小時候聽說他是回族,家里老實,可到了血火年代,他成了回民支隊的主心骨。說“百戰(zhàn)百勝”,這是毛主席的褒獎,但馬本齋心里大概明白,勝,是勝了許多沒有名字的犧牲。冀中平原,炮火間,馬本齋帶兵殺敵,也捱過苦,失過親。在外面人喊英雄,家里人卻只想他能平安回來。馬本齋的故事,到最后總帶點淡淡的悲劇——英雄,到底也是血肉凡人。

說起霍元甲,不提“精武會”,就是浪費。他祖上是滄州人,但生在天津,每天挑柴去城里賣,和后來那些武術(shù)名師的生活比起來,可真是天壤之別。小時候身子弱,人都不大看好他。“迷蹤拳”是家傳,可要真練到家,不是光靠幾下花架子。他直到快到不惑才被“看見”,在碼頭、在藥棧里,靠一身本事混飯吃。后來到了上海,把一身拳腳教給更多人,那會兒中國人在異國人跟前總被看扁,霍元甲偏不信邪。他拳上一撐,底氣就有了。如果你問霍元甲成功的秘訣,說不定一句“餓著肚子也不能丟了根骨”才是真理。
其實河北滄州這地方,風水輪流轉(zhuǎn),誰都不知道下一代還能出什么樣的“人物”。有人成名后猶如明燈,有人則像燈影下默默的那只蚊子,不叫喚,卻也活得認真。歷史的長河里,這些人的故事,被后人翻來覆去講、寫、記,有的流傳,有的消散。

我們常說,一方水土養(yǎng)一方人,可水土之外,還是那些無數(shù)日夜里,人和人的相逢、別離、掙扎與自省。滄州給了他們出發(fā)的地方,又送了他們到時光的彼岸。
下次路過滄州,你會不會想著,腳下的地,也許埋著一段未完的故事?那些舊書里翻出來的名字,會不會偶爾飄到你心里,留下點什么?這一切,也許都只是我們聽故事時的自作多情,但說不定,也正是這樣的“多情”讓歷史里的那些人,離我們不那么遠了。